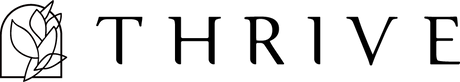Caravan Earrings 旅隊耳環
- 商品簡介
- 注意事項
- 出貨與配送
- 關於退換貨
-日本米珠、奧地利/捷克水晶珍珠
-耳勾/耳夾皆能訂製
-長約6公分,寬約1公分
‹重複的形體、重複的排列、重複的路途、重複的風塵僕僕,商隊篷車緊跟著前方夥伴的背影,這絕對不是一次悠閒順風旅程。›
距離Malik在齋戒前一晚隨著寶石商離開宮殿踏進荒沙已經過了兩週,預期會追擊過來的哈里發軍隊尚不見蹤影,但他的目的地也仍遙遙無期;他騎著列隊最後面的駱駝,打開水袋啜飲幾口,他最珍貴的愛人則待在離他最近的四輪篷車裡,免於被炙熱午燄燒灼。
第四十次月昇,有三隻駱駝病倒了,這使得整個商隊速度慢下許多。寶石商人順了順蓬鬆的大鬍子,佈滿皺紋的眉頭糾結,他的侍從們連一聲都不敢吭,只是把更多的水和牧草分配給隨行的黑色馬匹們——上好的阿拉伯種馬,將會在大隊抵達君士坦丁堡後,被分送到大陸最西邊的金髮人王國。Malik從來沒去過那邊,只聽說佈滿綠意的土丘平原取代了他在家鄉看得熟悉的沙丘。
又是一個黃昏,當Malik再次回首,眼角不停浮出扭動的蜃樓消失了,哈里發飛揚的旗幟以及甲冑映上的夕陽閃光才是他真正要擔心的危機。寶石商人舉起包覆著絲緞的棍鞭,輕拍了胯下的駝獸,快速掉頭到萎靡的隊尾。
「你,往北邊去,快去。」老商人大聲說著,一手拉著韁繩,空出的那手對侍從做了幾個手勢,一匹黑馬被帶到Malik身邊,重新繫在駱駝的右後側,另一位侍從則鑽進篷車翻找,等他再度出現,懷裡抱著一個密合著、以白銀雕花及青金石裝飾的寬口銅甕,Malik稍微彎下身子,小心翼翼接過銅甕,再放進掛在駱駝左側的旅行囊袋。
「這邊是額外的水和食物,不多,好好利用。」老商人匆匆喊著,疲憊的嗓音被逐漸逼近的一波巨大蹄聲蓋住。還來不及答謝,他的棍鞭一揮,駱駝與黑馬一齊撒腿狂奔,掀起了棕紅沙塵,Malik穩住身子,將身下的動物導航到該去的方向,投身到沙漠的黑夜。他在港口賣掉了黑馬和駱駝,換得一張船票和足夠的儲糧,銅甕在背包裡沈甸甸的,代表安全——他想著,跟著乘客魚貫登船。
到金髮人的國度時,Malik已無任何盤纏,只有包裡那只華美的銅瓶;他學習了當地的語言,在村裡以鐵匠的身份暫時待了下來,他知道自己不能公開朝拜他認知中唯一的神祇,另外做了小小的銀十字架掛在胸前,這樣法蘭克國王的巡守隊行經村落時才不會對黑髮濃眼的他起太多疑心。
第十個夏季結束前Malik揮別這個小村,繼續往北行,這兒有滿滿的蓊鬱森林,潛步之中只能見到絲縷陽光散射下到跟前的落葉,一切都跟他的童年相異,視覺、味覺、聽覺。諾曼大區很冷,他用自己鑄造的幾把好刀換了厚實的毛皮大衣。雪落的那天他在客棧內用餐,跑出門驚呼著;雪花停在他彎曲的長睫毛尖端,不消幾秒化成清水。
操著不同語言的另一個王國就在海的另一端,「英格蘭人。」賣漁婦指著灰色的海平面解釋,一邊熟練地剖開魚肚。雖然天色比起上一個村難看許多,但Malik決定先留步於此,一樣張羅了他打鐵鑄件的小舖子。春風讓諾曼地添了點生機,鮮豔的野花讓他想起老家的馬賽克壁畫。第十個冬季已經結束,當他把一枚銀戒調整到村裡準新娘Maria的手指尺寸,並牢牢鑲上一顆他好幾年前從大漠帶走的紅寶石,抬頭一望,是巡守的法蘭克士官。
「你不是本地人。」士官平靜而有禮地道出,銳利的藍眼被淺色的睫毛遮著。「王宮裡聽說了你的技術,因此我們要帶你走。」
Malik只有一個要求:給他一天一夜向他的愛人道別。他回到家,拉開床底的活板門,為防時不時路過的丹人強盜而建造的,粗布包覆著的是那只精緻銅甕。他給馬兒裝上鞍具,帶著甕,午夜前往海邊出發了。
二十年後策馬的速度當然不同於青年的氣盛身手,花了點時間他終於聞到海風和成群海鷗的鳴啼,晨曦透著低矮的雲朵掃過諾曼的海灘,濕黏泥沙巴著她的雙腳;他耳聞過法蘭克人的王宮有什麼,絲綢、寶石、宴席,但對Malik來說都是些黃金和石頭打造的牢籠,和呼羅珊的綠洲高殿大同小異。
他扭開了二十年從沒動過的甕蓋,甕身的雕刻還是那樣地精美細膩,裏頭存放的是骨灰。Malik繼續前行,直到鹹水淹過他腰際,緊緊抱著銅甕在胸前。日昇背著他,水很冷——夠冷,Malik心想,這樣的冷度一定能熄滅火刑帶來的劇痛。
手盛起來的灰燼很快地被海水吞噬,黎明稀疏的光斑隨著緩浪推移著,留戀在Malik的掌心和指縫間。
/
「你的愛人,他叫什麼名字?」士官長頷首。Malik思索著,二十個年頭,從沒人丟出這樣的問題,二十個年頭間他也沒有再提起這個名字。
「Altaïr。」最後,Malik輕聲答,喉頭盡是不捨悲傷,但忍下了淚滴,為了讓他的愛人永恆安息。「Altaïr Ibn-LaʼAhad,在你們的語言是飛鳥的意思。」
- 商品串珠主體皆為高拉力的專業編織用線材串成,請避免怪力拉扯、重物壓迫或高處摔落,以免五金變形或串珠碎裂。
- 金工或金屬產品因時間與濕度有氧化情況為正常現象。
- 鍍金黃銅部分請盡量避免碰到水或化學液體,請勿佩戴至有硫磺溫泉等地區。
- 平時不配戴時可以乾布擦拭,若要沖洗請使用清水,並於洗淨後徹底烘乾擦乾,可放入塑膠夾鏈袋隔絕空氣減阻氧化。
- THRIVE 繁生商品為手工製作,採接單訂製的方式出貨。
- 一般出貨日為訂購成功後的 7 至 21 個工作天(不含假日或國定假日)。
- 現貨專區商品約 3 個工作天即可出貨。
- 急單或其他特殊需求歡迎提早來函透過客服討論。
- 由於每件商品製作時間不同,原則上會等待所有商品製作完成再一次寄出,如無法等待請分開訂購,感謝您的耐心等待與理解。
- 國內出貨為加快與簡化出貨流程,出貨預設為中華郵政掛號。如需使用7-11店到店取貨請私訊官方IG提供訂單編號與收件資訊。
- 國外寄送依據地區不同可選擇中華郵政掛號、EMS、DHL或是順豐快遞。
- 郵寄本島需要 2 至 4 日寄達,外島需要約 7 日寄達(不含假日)。
- 7-11店到店取貨需要約 2 至 3 日寄達。
- 國際配送由中華郵政掛號、順豐快遞或其他物流服務寄出(根據國家不同),約需要至少 7 至 30日寄達。 若有特殊急用狀況皆可來函協議使用其他快遞服務。
- 單筆消費金額滿 NTD.6000 享有國內免運費,滿 NTD.12000 享有國際免運費。
- 本公司開設統一手寫發票(二聯式),原則上隨商品一同寄出,如需將發票另寄於其他地址或是需要開立三聯式統編發票,請在訂單的備註欄中註明需求,我們會另以一般信封掛號寄出。
- 依照消費者保護法規定「 THRIVE 繁生 」提供消費者網路購物七日鑑賞期(包含假日) ,退換貨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保持商品包裝、贈品、標籤、等之完整性) ,否則恕不接受退換貨。
-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及基於個人衛生考量,「 耳針款耳環不適用網路購物七日鑑賞期 」,除非商品寄錯或是瑕疵,一但售出後不提供退換貨服務。
- 換貨僅限出貨錯誤或瑕疵商品,例如:收到商品時嚴重斷裂破碎(不包含接合處線頭、金屬正常氧化、各式天然原料與金屬上的斑點痕跡,或包裝上因運送導致的擠壓變形破損)。
- 商品照皆為實品拍攝,因螢幕顯色、光線或個人觀感定義不同,難免有色差問題,請以收到的實際商品為準,色差並不屬於瑕疵範疇。
- 珍珠、貝殼、天然石等素材,花色與形狀沒辦法完全相同,出貨時我們會盡量搭配成對寄出,些微花色與形狀差距不屬於瑕疵範疇。
- 特殊活動之商品(如私人訂製商品、出清折扣商品等),則不提供因個人因素退換貨。
- 個人因素的退換運費由買家自行負擔 ,出貨錯誤或瑕疵商品的退換運費由「 THRIVE 繁生 」負擔。
- 如因個人因素退換貨次數過多,本公司將視情況決定是否暫停出貨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 為加速退款流程,退貨時請將發票一同寄回。
Caravan Earrings 旅隊耳環
- 最近瀏覽